仅支持付费会员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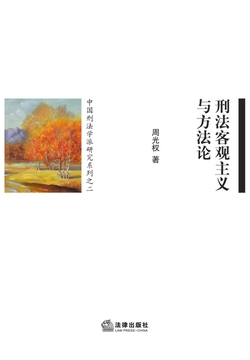
最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刑法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合理借鉴国外(不仅仅是德、日,也包括英美国家)最新理论,以建构精巧的刑法学体系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思考中国转型社会的特点,巧妙地回应社会需求,使刑法理论尽可能与司法实务相照应,可能是更需要深思的复杂问题。而在上述关键点背后,都明显隐含着一个刑法的“学派之争”如何展开、刑法基本立场如何定位的问题。必须看到,德国刑法学之所以在今天令人叹服,与圆园世纪圆园年代之前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全面交锋、圆园世纪中期开始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争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学派之争”,就没有今天德国刑法学蔚为大观的理论构造。日本刑法学的发展也没有脱离这一规律。但是,在中国,从总体上看,刑法学者自身立场的一贯性还较为缺乏,没有一个统一的、基本的逻辑体系。例如,某些学者在分析疑难案件时,总是习惯于从主观要件切入;在论述行为论时,强调犯罪客观面的重要性,但对未遂犯的成立坚持主观立场;在涉及教唆犯时,赞成共犯独立性说或“二重性说”,主观主义明显成为指导观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立场的缺乏导致“学派之争”在中国难以展开。虽然欧陆刑法上的“学派之争”是一个多世纪前出现的历史事实,但是,中国刑法学如欲取得长远发展,就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并要有展开“学派论争”的自觉。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当下中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尤为重要。
简介
最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刑法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合理借鉴国外(不仅仅是德、日,也包括英美国家)最新理论,以建构精巧的刑法学体系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思考中国转型社会的特点,巧妙地回应社会需求,使刑法理论尽可能与司法实务相照应,可能是更需要深思的复杂问题。而在上述关键点背后,都明显隐含着一个刑法的“学派之争”如何展开、刑法基本立场如何定位的问题。必须看到,德国刑法学之所以在今天令人叹服,与圆园世纪圆园年代之前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全面交锋、圆园世纪中期开始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争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学派之争”,就没有今天德国刑法学蔚为大观的理论构造。日本刑法学的发展也没有脱离这一规律。但是,在中国,从总体上看,刑法学者自身立场的一贯性还较为缺乏,没有一个统一的、基本的逻辑体系。例如,某些学者在分析疑难案件时,总是习惯于从主观要件切入;在论述行为论时,强调犯罪客观面的重要性,但对未遂犯的成立坚持主观立场;在涉及教唆犯时,赞成共犯独立性说或“二重性说”,主观主义明显成为指导观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立场的缺乏导致“学派之争”在中国难以展开。虽然欧陆刑法上的“学派之争”是一个多世纪前出现的历史事实,但是,中国刑法学如欲取得长远发展,就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并要有展开“学派论争”的自觉。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当下中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尤为重要。
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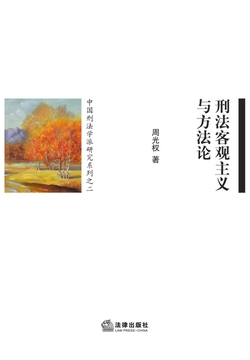
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
- 扉页
- 书名页+书签
- 版权信息
- 总序
- 作者简介
- 序言
- 上篇 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展开
- 第一章 刑法方法论的中国意义
- 第二章 刑法方法论与司法逻辑
- 第三章 客观归责论的方法论意义
- 第四章 刑法客观主义与共犯从属性说
- 第五章 价值判断与刑法知识转型
- 第六章 刑事指导案例制度的难题与前景
- 中篇 刑法客观主义与证据运用
- 第七章 刑法客观主义与非法证据排除——刑法和刑诉法的“交错”
- 第八章 刑法与控方证明责任
- 第九章 明知与刑事推定
- 第十章 受贿罪的认定与证明标准
- 第十一章 渎职犯罪的指控难点
- 下篇 刑法客观主义与刑罚适用
- 第十二章 量刑程序改革的实体法支撑
- 第十三章 量刑上的禁止不利评价原则
- 第十四章 禁止重复评价
- 第十五章 刑法客观主义与教唆犯的处罚
- 第十六章 刑法客观主义视角下的立功
- 第十七章 刑法客观主义与犯罪数额计算
- 参考文献
- 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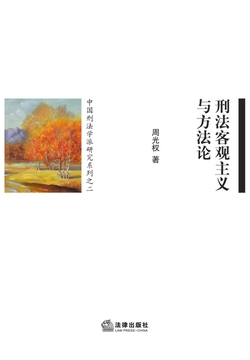
想法、划线、书签
仅支持付费会员使用
仅支持付费会员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