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作者的搜索结果

传统文化生态观的教育传承研究
传统文化生态观主要体现在村庄聚落,真正的实践层面也几乎就在乡村社会,其具体的表现方面非常繁复,一般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描述,一是形而下的实践层面,二是形而上的观念方面。形而下是主要的关注对象,因为村民不可能有更多的理论思考,主要体现在实践中的遵循与运用,因此选择农业最为常见的生产生活,即农业生产、山林狩猎和房屋建筑,从中考察这些方面体现了哪些生态思想。形而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理念,这是经过文人归纳、统治者认可的理论。基于此,我们将乡村生活从教育层面进行必要归类,大体归纳为行为教育、规约教育、敬畏教育、威权教育等几个方面,并对此教育方式与效果进行探析,得出各自的特点,为传统文化生态观的教育传承做出点贡献。

穿越历史隧洞的客家人
每个族群都是从历史穿越而来,贺州客家从明清走来,从弱势族群成长为优势族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获得长足发展。历史的穿越性使得贺州客家获得许多历史遗存,由此建立了广西第一个客家族群文化生态博物馆,成为贺州极力打造的文化品牌。透过活态的历史遗存,不仅能够探知客家人的内在心路历程,还可以展望未来发展路径,给予全球化背景下的族群文化发展提供借鉴,有效地实现从历史走向未来。

农村新民居审美研究
农村新民居在城市建筑时尚引领下,大量地出现水泥楼房建筑。这些水泥楼房单体民居,从外到内都包含着不同于传统旧民居的因素,不仅只是外在的新,还包含深刻的现代信息,使之真正变成现代建筑。由这些新民居组成的新聚落,不同于旧民居构成的旧聚落,展现出新的特质,携带明显的现代信息,也使得聚落变成了新时代的聚落。这种时代性反映在多个层面,诸如出现了空心村,聚落由传统集聚式向零散化转变,更向村道公路聚集,村庄间距由清晰变成模糊,总之,已经完全不像传统的村庄聚落形态。

客家人生态性生存
客家人在不断地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民性,也寻找到了适于族群生存的生态性生存技巧。客家人不仅主动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主动适应居住地社会生态环境,而且还努力创造适于族群发展的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居住地主体族群。贺州客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们于明清时期主要从广东入迁贺州,主动适应贺州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环境特点,因此先其而居的土著本地人并没有采取驱逐政策,而是怀着极大的容忍度接纳新来的入迁者,大家就在这块土地上共同生活。在这种和谐的族群社会生态环境下,贺州客家人逐渐从弱势族群发展成为优势族群,虽然其人口数量不及本地人,但在社会生态环境中已经显现出某种优势,拥有相当大的社会话语权。贺州客家人的这种生态技能,不仅表现客家人的生存智慧,也值得各个族群借鉴。

空心村乡村文化研究
打工经济不仅改善了村民生活,而且造就了候鸟人,影响着乡村的农业生产,真正造成了无人的空心村。空心村依然从事着农业生产,但是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生产。传统的农业思想已经发生隐性变化,原来厚重的农业地位已经变轻,对于土地的情感也开始发生变化,呈现出现代文明影响的特征。在这个转型过程,原有的耕作方式和亲情平台,都被迫相应改变,虽然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还没有明显改变,但是也出现一些潜在的隐约变化,而显性表层的东西改变较为明显,传统节日习俗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乡村权威正在消解,年轻人的话语权正在彰显,村民的个性也得到有效张扬。乡村作为一个符号,内中包含着血缘、地域、地域、文化、乃至法律等各个方面的文化信息,因此始终还是村民不能割舍的精神纽带,能够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瑶族文化之教育传承
瑶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这是民众和学者的普遍看法。其实,瑶族的迁徙状况比较复杂,既有经常性迁徙,也有宽定居窄迁徙,不可一概而论。而且,迁徙也有不同情形,既有主动迁徙,也有被动迁徙,这些迁徙隐含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一种生命自由的崇尚。这样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并不以系统的理论呈现,而是融入日常生活,通过姓名、居所、婚姻、服饰和信仰等多个层面表现出来,都倾向于追求生命的和谐。在没有文字且严重缺乏体制内学校教育的情况下,瑶族以其独特的行为教育方式有效地传承着自己的这种生命和谐的民族文化。这种传承既保证了瑶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又体现不同支系的族群文化特点,值得我们探索与学习。将这种教育精神运用到审美化课堂教育,既能够舒展一种生命的和谐审美价值,又能够提供一种课堂教学借鉴,确实不失为一种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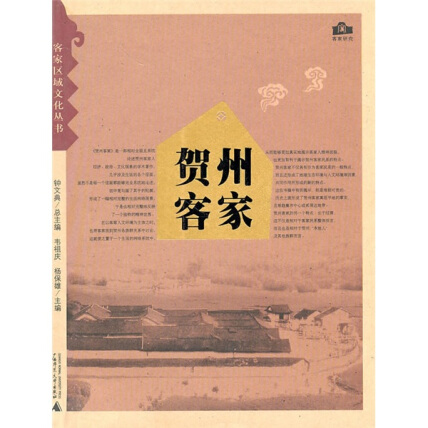
贺州客家
本书是一部相对全面且系统论述贺州客家人经济、政治、文化现象的学术著作,几乎涉及生活的各个层面,虽然不是每一个层面都能够完全系统地论述,但毕竟勾画了其中的轮廓,形成了一幅相对完整的生活网络图景,于是也相对完整地反映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在以客家人文环境为主体之时,也将客家放到贺州各族群关系中讨论,这就使之置于一个生活的网络系统中,从而能够更加真实地揭示客家人精神面貌,也更加有利于揭示贺州客家民系的特点。